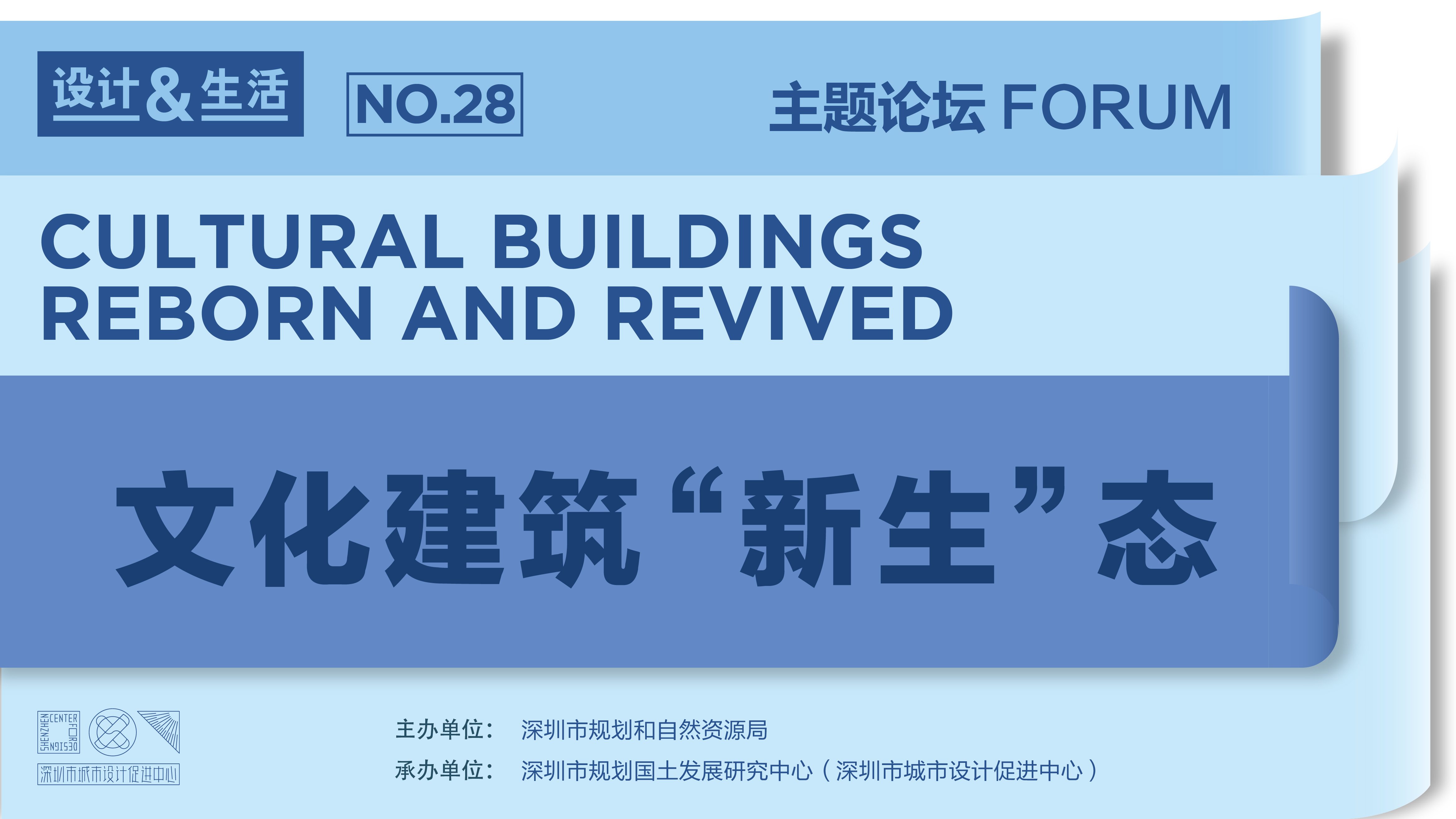从城市更新想开去,空间、城市与人

2016-06-03

艺象iD TOWN国际艺术园区
13518 人阅读
摘要:
“我们不应该去纪念那些现有的建筑,而应该去纪念那些被拆的建筑。”
刘磊
主持人
深圳市城市设计促进中心总监
何健翔
源计划创始合伙人、主持建筑师
梁田
艺象iD TOWN国际艺术园区总负责人
杨阡
自由艺术家、编剧、社会公益践行者
活动回顾
嘉宾对谈
深圳在发展过程中,把团结人的空间变成了区分人的空间
杨阡:我们不应该去纪念那些现有的建筑,而应该去纪念那些被拆的建筑。
今天我们谈的是一个和城市记忆,包括城市活化甚至是遗址、废墟,是这些层面上的东西。改造建筑,或是全新的设计,然后赋予它以一种新的姿态,不论是形式还是内容,更多的时候还是一种功能的暗示。如果从细小的角度介入到这个话题中的话,我认为我们一直在做的事就是怎样去想象空间,也就是讲什么故事。讲了好几年的故事之后我发现,实际上在空间领域找不到一个真正属于全体深圳人的空间。如果大家仔细去看我们熟悉的建筑,市民中心应该叫做最大的公共空间了,但你认为它属于你吗?肯定不是。现在的深圳湾公园,从东边一直蜿蜒至蛇口,是一个沿海休闲带。那个公园属于你吗?好像有一点属于你,但好像也不是。我想说的是,在我们这个城市系统里,空间是用来团结所有人的,实际上,空间主要是用来区隔人群的。换句话说,什么空间只能由什么人来用,什么空间只能由另外一群人来用。这样的空间消费只能是属于这样的一些人,那样的空间消费只能是属于那样的一些人。所以最后我只能说唯一属于我们深圳人的空间是那些失去的空间,这就是我想说的。
再论什么样的城市是好的城市
梁田:我觉得开放和公共性,是我非常重视的一件事。这个园区在我的概念当中一定是开放的,我希望能有更多的朋友来打开更多的窗。
刘磊:现在的iD TOWN像一个城市,它在逐渐生长,很多新注入的活力其实已经超脱了建筑师和建筑审美的控制,在建筑师营造的唯美、肃静的空间中,开始允许更多的多样性进来。
杨阡:建筑师还有艺术家能够有机会做新的空间挖掘,我觉得这对于我们的城市来说是一个绝好的机会,某种意义上讲可能也是我们城市的一种骄傲。从城市的角度来说,自简·雅各布斯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之后,社会已经基本形成了一种共识,我也希望这种共识在中国的城市年轻的公民身上扎根。
什么是好的城市,什么是坏的城市,判断这件事实际上有个一个基本的标准。好的城市,就是不论你受过多少教育,小学也好,文盲也好,博士后也好,没有关系;不论你经济实力大小,亿万富翁也好,乞丐也好;不论你的肤色,黑人也好,白人也好,黄种人也好;不论你的信仰,天主教徒也好,佛教徒也好;不论你的性别,女性、男性,亦或是双性者,无所谓,只要在这个城市中,人人都有机会发展,都能获得他们的成功,这样的城市就是好城市。反之,只有一部分人能够获得成功,然后朝着自己的方向发展,这样的城市是不好的城市。如果大家按照这样的标准去看,深圳哪个区域更像是好的城市?仔细想想,城中村其实是好的城市的楷模,是让所有人都能够获得发展的地方。我希望大家好好去看一下城中村,甚至在那里生活一段时间,你会体味到城中村的那种优美。
何健翔:城市之所以成为城市,或者说,为什么当代的文化、当代的艺术基本上都在城市中成长,正是基于城市的包容和多元。在欧洲有很多中世纪的城市,最早是教会在那里建了教堂、修道院,接下来围绕这些建筑形成商业,然后慢慢形成一个城市。从城市承载的角度来看,我觉得iDTOWN有些类似这样的状态。
对空间进行更新,建筑师需要更多地参与社会生活
何健翔:我们这几年做了很多与城市记忆、城市更新还有旧工业改造有关的项目,同时我们也在做一些新建。与新建相比,旧的会更快,同时我们也可以根据空间呈现出来的不同状态不断地做出一些更新,用不同的策略和方法来延缓,或者说至少是干预城市消灭一切蔓延的进程。就像是一个个小绿轴,你做了一些事情产生某方面的影响力,甚至是能够带来一些新的观念,这是一个非常享受的过程,并且,不论是设计还是建筑,都非常需要这样的做法。
我的同事在广美带研究生,教他们理论课。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对旧东西的关怀或者说是关心,是对现有教育状态的一个很好的补充。在传统的建筑教育里面,建筑师的训练就是要描绘一个新的蓝图,实际上这是一个狭窄或者说是有点可怕的事情。在这种状态下,你不会关心任何现存的东西,不管是土地、湿地,还是现有的花花草草。“去创造”这件事情,不论是基于资本的需要还是人的需要,亦或是建筑师自身的自大,某种程度上都会有一些过分自我的表达。实际上,建筑是很特殊的,它必须坐落在每块土地上,不管是五年还是十年,建筑都必须参与到社会生活里面。我觉得,如果建筑师能够留意到并且真正关心老的东西或者周边的环境,将会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过程。它有点像一个对话,当你与环境开始对话,当你慢慢去认识环境之后,你们之间就会产生一些深刻而有感情的东西。
公众交流
01 房价这么高,深圳真的是个友好的城市吗?
我刚来深圳四年,我有些朋友已经回去了。昨天我跟朋友探讨,他觉得深圳是不友好的,房价是个很大的问题。所以我想请各位嘉宾老师探讨一下怎么样的城市是更友好、更包容的城市?
杨阡:我觉得友好和包容的城市应该是一个可以谈判的地方。举一个例子,我自己的亲身经历。我那年去纽约大都会看歌剧,穿着一条牛仔裤、一件T恤。检票员穿了一身燕尾服,很高大上的。然后他把我领到最后两排,是一个廊子,你可以趴在那儿或是站着,但是那儿有一个扶手,不会累。我就在那儿站着,我想不对,我得去找他。我让他看我的票,然后他看看,说了声“Sorry”,然后把我带到第五排中间的地方让我坐下来。我是说有些时候,在一个有门槛的系统里面,工作的人员是有下意识的,也是我们经常看很多政府的官员。最典型的就是最近雷洋那件事,你抓我,我肯定打你了。他是一个习惯,在任何一个有系统的门槛的系统里面,人就有了一个情景。我个人的看法是原来深圳好一点,就是说深圳很多门槛之类的有意识的降低或者是至少即便是有的话,在里面的人也有某种礼貌和不是那么高高在上,但最近很多地方态度就是先拒。我觉得重要的一个地方是先不拒绝,然后是可以谈,我觉得这两条可能是关于友好的一个来源。
何健翔:我说两句,像深圳这样的城市确实现在的状态跟前几年有比较大的变化,无论你说房子还是领域的一些问题确实会存在,所以我觉得从管理或者运营的层面也要做调整,比如说有微型公寓的政策,提供一些满足条件的比如在深圳工作前几年的,就是要平衡。就像税收高了是否用另一种政策补回来,这是成熟的城市应该去有配对的措施。
杨阡:白石洲现在有一个专门的社工组织在做,它就是按照你来深圳的时间,然后按照你的收入租给你,而且它会帮你寻找就业的事情,相对来说是非常便宜的,现在社会服务也开始慢慢专业化了。
02 在城市更新过程中,我们应该如何平衡新与旧的关系?
公众2:我本科是在东北大学,东北大学处于沈阳,因为铁西区有苏联人过来设计的小区。我们原来做铁西区工业影响再改造的时候也对生活方式有保留,包括现在改成生活区的生活馆、纪念馆,原来的生活方式包括家具的布置现在也一直在保留。我感觉每个城市都应该是在更新过程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名片或者是符号,让大家进入到这个城市中见到这个东西就知道这是城市独有的。而现在感觉大家去去其它地方旅游,看到好多的都是钢筋混凝土大的建筑,我们找不见独有的。所以我在想我们在做大范围城市更新的时候怎么保证这些元素跟城市同步的更新改造,让他们渐渐适应城市高节奏的生活而不被城市所抛弃。
杨阡:我还是回到刚才问题的起点,我们的历史观某种意义上讲是这样的,我们的历史观是要日日新、再日新、更日新。于是乎,我们有时候受不了自己的过去。这种态度对所有的包括对我们的生活习惯、饮食起居,也包括对我们曾经待过的空间。照理说这是二三十年的历史,就很匆忙把它拆了。我想说的其实是我们的态度、价值观决定对事物的去留。你恨你父母吗?不恨。我告诉你,文革的时候我恨我父母,是我们过去的经历,我觉得人需要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好的情感状态、比较好的态度,然后你对于周围的事物似乎会慢慢的先接受,然后对话,再考虑去留,我觉得是这样的情况。我觉得这跟内在的生活有关,实际上内在的生活,外行对这个世界改造的行为想法。
何健翔:因为你是学城市设计的,我觉得你的思考里面可能要更尝试去找到突破口,因为你问的问题还是从道德的角度,我觉得还是比较简单化的。一个城市有一个老的东西是名片,但实际上你如何设计这个城市,你至少要理解这个城市运作的机制或者背后的游戏规则,你才有可能。不可能拿着一般份设计案说这就是对城市好的,因为它保留了这个。前天我在看研究生的设计本质上都是这样的状态,我给这个村落的村民设计了这样的东西,最后谁会投钱做这样的设计呢,你怎么样才能做呢?我不是说这个事情是错的,而是要尝试理解得更深刻一点才有可能去做。实际上中国人也很简单,在中国社会里面人是非常简单的,如果做一个事情有利益和回报自然就会去做了。实际上中国人比西方人还要简单,实际上中国人更加务实,如果做这个事情,在城市里面,比如说深圳为什么文化设计这么兴旺,就是因为好的设计做了能拿到项目,能建成,有他的回报,所以这里有设计文化,就这么简单。实际上城市是这么运作的,不是简单说要保护这里,如果光是这么想问题的话,你很难真正有效的规划跟设计一个城市。
公众3:我感觉一个最有效的方法是我们应该探索出让政府、设计师、居民多角度、多方面衡量的利益点。
何健翔:实际上这是城市里面不同的人在里边玩一个大规模的、大范围的游戏,你要打通了才有可能。你懂这个东西不等于你要参与这个事情,你不一定要参与这个事情。你不懂得的话,你是没有办法参与和有任何的影响。
梁田:无论是对于现在城市面貌的惋惜,我可能曾经也是跟你一样的,更多的是从游客的角度感受说为什么不能是这样。从运营上来说不在于尝试探讨,在探讨之前你先尝试你的对立面看他们是不是这么想的。这就跟谈恋爱过程中,大家吵架了,实际上有没有尝试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想。
03艺象iD TOWN如何才能在众多的文化产业项目中脱颖而出,彰显自己的个性和价值?
公众4:四位老师好,客观地分析一下,艺象iD TOWN的招商优势现在是没有办法体现出来的,第二个是它的规模也不是特别大。现在虽然是一个信息时代,但是入驻这里的可以通过互联网好好的沟通,但现实是我们现在具有越来越多面对面的交流,所以这些企业在招商的过程中怎么考虑这些问题?以后是不是有手工坊、咖啡店、书店等,你怎么运营计划,就是说不要再跟别人一样弄一些一致性的东西出来把这里弄得跟华侨城差不多,而是说真正凸现真正的价值。
梁田:坦白说,从我内心来讲,大家都有一句通俗话说“屁股决定脑袋”,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从我内心,一百个人可能有一百种吐槽华侨城的点点滴滴。但在我来看,华侨城没有任何不对,只是它这种状态是你不喜欢的一种状态。当然我也很愿意像你说的有更多的内容或者新的形态、新鲜的玩意儿,我也很愿意,毕竟这个园区所在的地方是在大鹏相对广义上的旅游景区之内,所以它还是会被动的一定会承担一部分功能的在里面,所以说这一定是我们的方向。但还是回到刚才那位同学的说法,何健翔刚刚说社区,它一定是一个双向的结果,那么也就是说我们运营方,我觉得比较好的方式是和已经来到、已经加入到这个园区的艺术家、设计师或者这样的人群,我们共同来想。如果这是我家的话,这不是我的家人,我是房东。在我们签完合同之后,我就不再认为我是一个房东了,大家是一个家,互相之间为这个园区、为大家共同的家做一点什么。当然,我这个想法大家觉得会有点理想化或者浪漫,但这是这个园区尝试性的一个方向所在。
何健翔:我也补充一下,我还是有一个坏习惯,对语言有点洁癖。在你的问题里面,我感觉到你问问题的前提还是带有常规的一种交通问题,就是分析一个地段或者分析问题,还是交通周边有没有配套、规模够不够大或者你有什么问题,实际上这还是一个常规的观点或者视角看问题。如果要做另类的或者尝试新东西,我觉得尝试要跳出这个常规的思维。我们太多先入为主了,做事情就是要先画一个图,你先画图纸。某种意义上真正要做好一件事情或者是做不一样的事情肯定是不能这样的,反而需要我质疑,有这样的一种观念,这个习惯会非常重要的,如果你想要做不一样的事情必须要挑战现有的东西。比如说一开始想做这个园区的时候,交通不便是摆在这里的,它不可能变成华恰成也不可能变成别的地方,它只能是它自己,它自己是什么状态,它自己就是远离城市,环境是非常安静的。尤其在当今的城市这么繁忙、这么压迫的时候绝对有人是希望避开、逃离这个城市,实际上这里是为了逃离而不是为了方便,为了方便的人不回来到这里。包括规模,实际上规模反而在这种状态下越小越有利,它都不是一个常规的,都是寻求不同体验的人所喜欢的。现在你也说了,互联网这么简单,所以宣传完全不是一个问题,以前还要想方设法怎么让人家知道,现在根本不用了,只要你把这个事情做好这是会自动传播出去。这里面有很多,如果你在享受这种不一样的我跟别人不一样,你会找出来很多新的乐趣或者新的体验,这种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杨阡:某种意义上讲,我在美国读人类学,人类学有一个挺逗的情况,我说的是西方人类学,它的发展实际上是相对于西方的社会学来说,西方社会学研究自己的社会,西方人类学研究它以外的社会,研究跟它自己不同的。我们前提的预设,它就跟我们不一样,它所有的价值正因为跟我们不一样,所以研究也不一样。
最近有几本非常著名的著作我推荐大家去看,一个是科斯特的《逃离帝国》(音),我们通常会说一个帝国是占有多大,比如说中华帝国,咱们拿清朝来说,它占有的从内蒙古一直到台湾这么大的片区。克斯特说不是这样的,某种意义上讲这些帝国围着太平洋沿岸大的帝国,他们只占有海拔300米以下的地方,海拔300米以上的地方不是他们的土地。换句话说,只有能种粮食,不管是稻谷还是小麦的地方才是这些帝国统治的地方,而在那之上不是。为什么他这么说呢?拿中国的故事就可以看出来,比如苗族、傣族、壮族其实是不断逃离大的帝国统治,他们不愿意成为帝国的人民,他们希望变成自由民,所以他们的生存方式就不是生产稻谷、小麦这些所谓的经济价值极高的作物,他们只生产比如玉米甚至是土豆作为他们的粮食。我们要看苗族的语言是退化的,原来说是有文字,后来文字没有了,只保留口头的传说,它的目的就是为了不变成一种帝国。那么下一个问题来了,除非你认为帝国才叫文明,那么那些人都叫野蛮人,这就是一个立场的问题。
第二个很伟大的一个学者叫大卫·克里特(音),其实他有三本书,一本叫《债》,还有一本是《我们为什么要上街》(音),还有一本是关于无政府主义的。他谈了一个很实际的问题是什么?他说我们今天太习惯于用今天的逻辑去推到变成人类的一个普遍的人性。举一个例子,在有货币交换之前,我们的经济学推论是物物交换,但是人类学不是这样的,最早期我们是一个礼物社会。换句话说,物物交换的前提是等价交换,就是你给我一瓶水我给你一馒头,我给你两馒头吃亏了。但是在礼物时期,如果我斤斤计较,这不光是对我,也对给我的人是冒犯,这样的问题跟我们的预设有关系。除非预想人类在一开始就愿意在统治之下的人之外,其他都不叫人,你才能设想。实际上人类的存在是多种多样的,我想在城市里面这个多样性不是在统一性之下,多样性是跳出在统一性之外的。蚂蚁群体里面是这样的,有一个动物人类学家也是灵机一动,看蚂蚁有很多工蚁、兵蚁,所以他们就把什么都不干的10%的自由蚂蚁全都拿走了,慢慢他们发现从工蚁、士蚁里面又慢慢的出现10%什么都不干的蚂蚁。换句话说,我们有一种习惯是为了适应显性的危机之内的,但是一旦有一个大的危机不能用我们这种方式适应的话,没准就是那10%发展出新的适应方式你就活了。我们不要不断的说这个东西是文明的,那个东西是野蛮的,也许错了,可能对于那个野蛮人来说你这个帝国的统治才叫野蛮。
何健翔:非常好的一个比喻,我在这里似乎可以设想另外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10%的时间是游离的这些状态之外,我觉得这才是最宝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