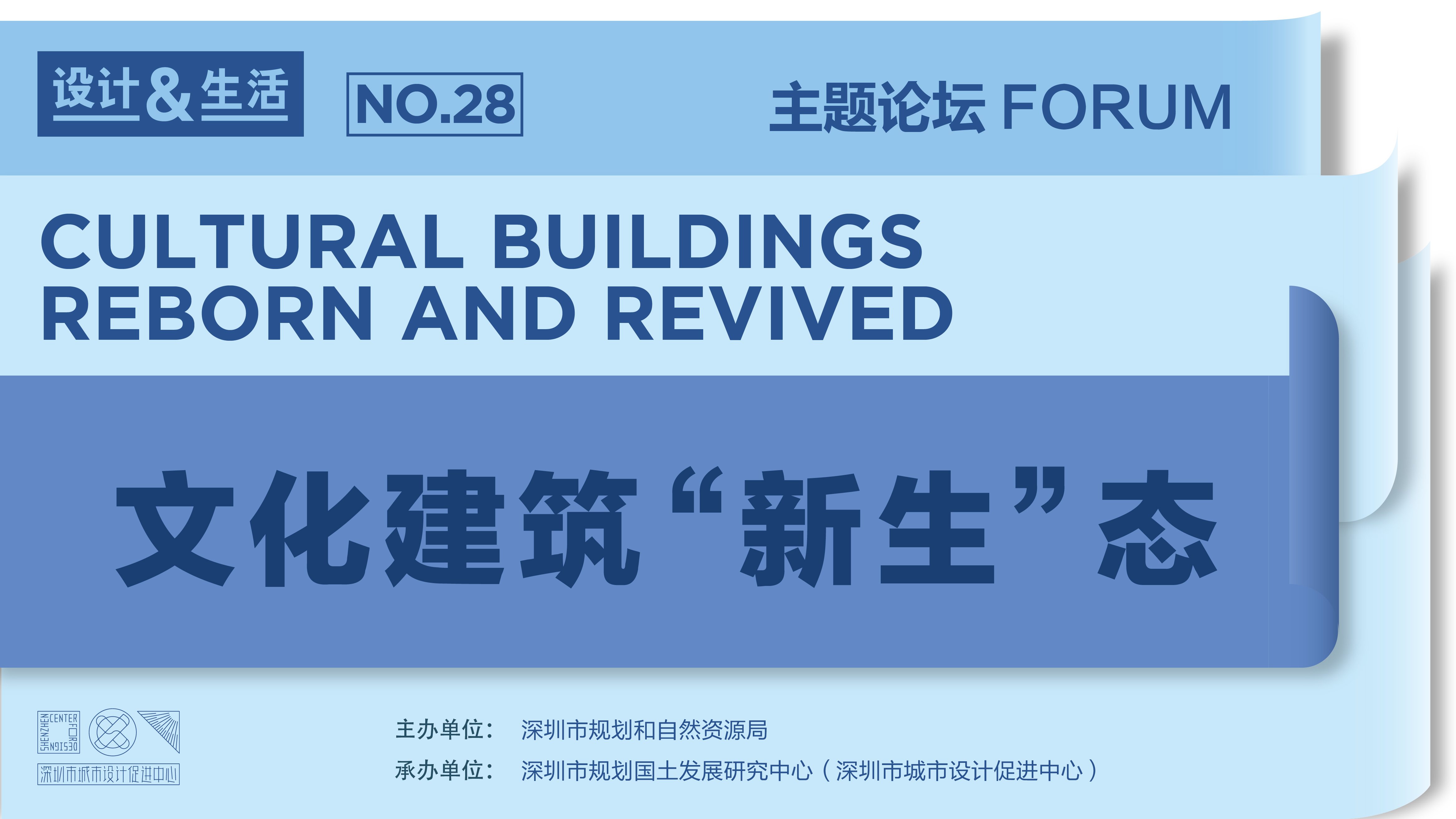深交所:库哈斯摩天楼的建筑类型学


14120 人阅读
摘要:
库哈斯的建筑常常有着简单却惊世骇俗的外表。就像建筑师事务所名称所暗示的那样,他的建筑“类型”最终取决于城市的上下文,在都市语境之中“它们”(而不是“它”)才有自己的意义,它的建筑类型学是城市-建筑的类型学。
活动回顾
编者按:本文特约建筑评论家、“设计与生活”公众论坛对谈嘉宾唐克扬老师为深圳证券交易所建筑撰稿。
库哈斯的建筑常常有着简单却惊世骇俗的外表。就像建筑师事务所名称所暗示的那样,他的建筑“类型”最终取决于城市的上下文,在都市语境之中“它们”(而不是“它”)才有自己的意义,它的建筑类型学是城市-建筑的类型学。
库哈斯的城市-建筑思想最初闪现于《癫狂的纽约》这本书。“以公平牺牲了美观”的纽约早期规划网格是曼哈顿建筑学浮现的前提,它有这么几个不同寻常的地方:其一,“网格”的构成,和未经开发的产业上的地形和地理条件没有任何关系;第二,它不预见会有什么样的居民和城市生活安置在那里;第三,它不预计这个城市未来的发展,而只是在各个可能的方向上随意延展;最后,它并不指定每个街区的形象和功能,每个街区间的空间关系是均匀一致的——相应地,在后来的纽约,垂直方向上的规划机制是“地面的一味倍增”,在书中谈到西奥多·斯达雷特(Theodore Starrett)在20世纪初期的100层摩天楼方案时,作者说,这个当时骇人听闻的方案与其是(在建筑学意义上)“设计”出来的不如说是(在工程学意义上)得到“解决”的。“网格的两维法则也为三维上的无法无天创造了无上的自由”,竖直方向上升起的摩天楼和网格一样是“一种概念性的投机”。摩天楼具有“吸引眼球的能力”和“占据地盘时的谦卑”,网格则在平面上具有“完美的承受性”。“在很多方面,作为一种卓然自立的、形象鲜明建筑的曼哈顿主义历史就是这两种类型学的辩证法。”
三十年来库哈斯对于摩天楼的态度并未变化,深圳证交所设计的意义因此建立在对于纽约和深圳,二十世纪初和二十世纪末时空差异的理解之上,这差异也自然导致了项目中被改头换面的高层建筑形式。在纽约的摩天楼里存在着外立面和里面内容的分离:外面让位给形象,里面由于新的交通技术(电梯)的存在,串起了一系列不甚相关的内容程序。库哈斯批评“曼哈顿主义”后来的死亡是因为过于“干净”的现代主义使得“聚集的狂喜”(mass exhilaration)——或者说,“都会情境里超高密度中的奇观和痛苦”——失效了,而他面对的当代中国的情形恐怕是这种困境之上的困境:一方面深圳也存在着他称颂的“自体的纪念碑”,他在九十年代所描写过的珠江三角洲的“大跃进”——一个几乎一夜建成的城市既成就了建筑,也确立了建筑的上下文;与此同时,这种巨无霸式的建筑发展,一个庞大的“物”内里的情形却怕不是他能控制的。和二十世纪初的纽约相比,甚至也和它的创生伊始相比,今天的深圳中心区慢慢失去了它的密度——不仅是物理和生活的密度,还有开发的和文化的密度——“拥堵的文化”的前提。
深圳证交所可以看成对这样的现实的一种回应。首先,它再次呈现出了“异体繁殖”( cross-fertilization)的顽强意图,那个空中的硕大平台,无论是在类型和意义上,都在同一建筑的内部造成了巨大的差异性,粉碎了摩天楼内均一的垂直网格。“裙楼”不再是摩天楼的附属成分,而是改头换面嵌入建筑的新变量。此处“混搭”是一种轻松而又严肃的游戏,它不仅仅是创造意外效果的外部手段,更是在城市里引入愈演愈烈的差别(exacerbated difference)的内设机制,“混搭”并不仅仅意味着视觉风格的多样化——这只是事后的结果——而且是功能-形式有意识的解体重组,它弥补了孤立于城市中的“垂直街区”在密度和混合上的缺憾。
如果能把OMA迄今提出的大量摩天楼提案(包括有名的CCTV方案)放在一起看,我们就会同意它们绝不仅仅是为“优美、有力的雕塑形象”而生的。事实上,OMA的作品集中有海量的未能实现的“混搭”项目,为了一个同样条件的摩天楼,自动“编排”的造型方案多达数百个。它们似乎验证着这样一个印象:它们是程序化“生产”的建筑,而不是象很多人渲染的,按经典方法推理出的类型学。人们可能轻易将这座建筑物的造型与它的功能——金融交易,市场经济的主要象征物——相联系,然而,这样的造型也可能出现在Tour Phare这样的巴黎观光建筑上,它们毫无疑问也是深交所类型的类型来源之一。就像密斯的西格拉姆大厦在纽约公园大道街面上著名的回缩一样,深交所悬空的裙楼下形成的广场不是针对特定功能演绎的专需品,相反它是对一般的当代城市状况的特定回应。
通过“一栋楼拯救一个城市”,库哈斯正从特立独行的都市主义走向特立独行的建筑类型学。在一个访谈中,库哈斯谈到他一贯的主张:“……太多的钱投资于细节,漂亮、优雅。但建筑不仅是这些,建筑还包括给予,包括功能。我想我们只能做这么多,今天我们更需要来自外部的建筑话语。但在同一个访谈中,CCTV的评委之一矶崎新却指出,“通常评委对于CCTV的期许是代表中国媒体的未来,国家级机构的形象。但CCTV并不是再现偶像(作者注:Icon),库哈斯所做的本身就是一个偶像,他把再现过程给反转了……”
从“城市主义”到“Icon”的转变,要结合2002年之后发生的一切来看待就会更加清晰,如同乔治·贝尔德所提示的那样,库哈斯的实践分别在80年代末期,21世纪初期发生了变化。作为库哈斯事务所最成功的现实项目之一,CCTV新楼和深圳股票交易所大楼象征着OMA一个阶段性的转折,那就是他的作品从纸上虚拟的全方位策略,演进为一座座终于“实现”——鹿特丹OMA办公室中口号的关键词——却孤立的“城中之城”。作为也就是他的客户们喜闻乐见的巨大“Icon”,这些建筑每一个都特立独行地吸引眼球——它们的“叙事强度被降低了,成了一种[类型学的]机械过程。”“我们现在并不缺少建筑,而是缺少标志性建筑,让每一个作品都充满个性是我的建筑理念。”有证据证明,这一切是设定好的,并非库哈斯一个人在设计,在CCTV之后OMA的万千“通用现代化专利”类型和它先前所发明的“版权所有”词语一样,成为公司运转的动力源泉。这些项目放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有始无终的过程,像是回到了建筑师早年的写作生涯。
库哈斯提示人们,这些支离破碎的、不甚“稳定”的“Icon”并不是雕塑性的形象,而是一种矛盾性过程的自然结果,他甚至用埃舍尔( Maurits Cornelis Escher)这样艺术家的例子来提醒他的员工,这种自我打破的开放性设计将保证OMA作品的新鲜程度。如果库哈斯的客户们不止是在一个地方注目于他的实践,也会同样恍然大悟:对于建筑师自己而言,这些实现或并未实现的方案其实是高度一致的,它们突破了严酷现实可能带来的保守和滞后,在每一个方案里尽可能地追求不合常情的突破,以创造出进一步“交叉繁殖”的动力,不停地“移植”是打破文明发展瓶颈的有效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