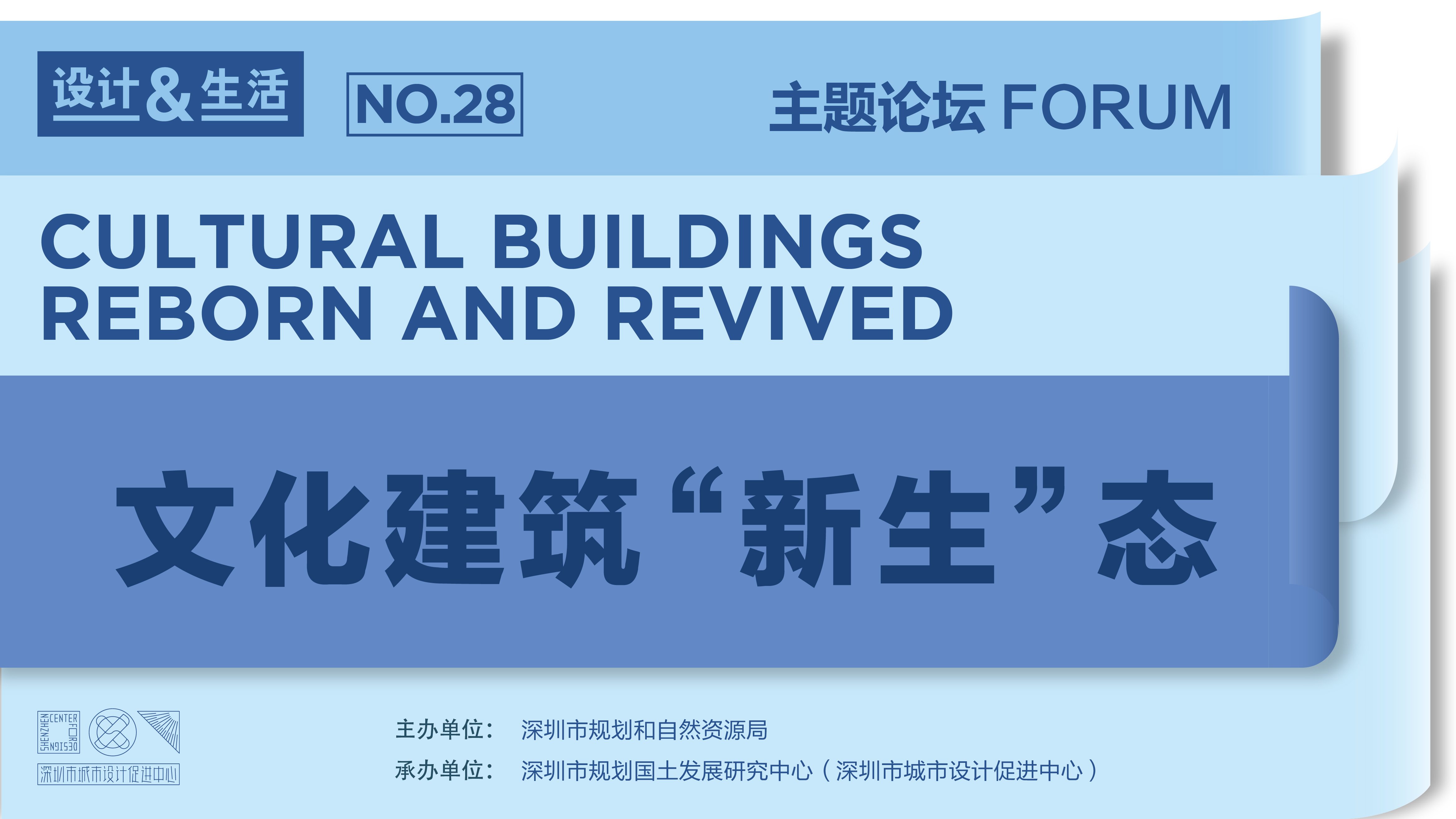走进红岭实验小学,看高密度时代下的新校园建筑

2019-11-23

深圳福田红岭实验小学
14914 人阅读
摘要:
近年来,为应对中小学学位需求激增的问题,深圳涌现了大量的中小学新建和改建项目。一批独立建筑师事务所积极参与校园设计,产生多样化的优秀原创作品。但同时,建筑师在设计实践过程中也需面对土地资源紧张的挑战和教育管理部门固定运营模式的协商问题等。校园设计规范是否跟深圳当前的城市发展阶段相匹配?是否能承载多元化和地域性的设计创新,以及是否对未来教育模式创新和新校园精神保持开放?
活动回顾
11月23日,第19期“设计与生活”如期举行。本期活动以“走向新校园——高密度时代下的新校园建筑”为主题,邀请了深圳福田红岭实验小学主持建筑师何健翔、蒋滢,“福田新校园行动计划”策划和发起人周红玫,深圳市福田区红岭中学(集团)书记、校长张健,共同探讨如何面对具体的使用需求和复杂的限制条件,在设计实践中植入对城市和时代精神的理解,挖掘当代校园设计的在地性。

活动当天由源计划建筑师事务所的创始合伙人,红岭实验小学的主持建筑师何健翔先生、蒋滢女士导览,带领近200位市民参观校园,讲解设计细节——大到校园的整体设计方向、小到教室的形状及灯光照度……
校园利用了所在地北高南低的条件,在校园“E”形平板上形成上下错动,营造了地景式的爬升;以“细胞单元”的概念设计可以自由开闭的教室空间,避免教室过长阻隔自然风,灵活的隔断方式回应了学校课程改革中混合式教学的需求;更有连接两侧庭院的阶梯式廊桥,给在校学生们带来独特景观和游戏体验。部分到场的建筑师以“震撼”二字来形容红岭实验小学的设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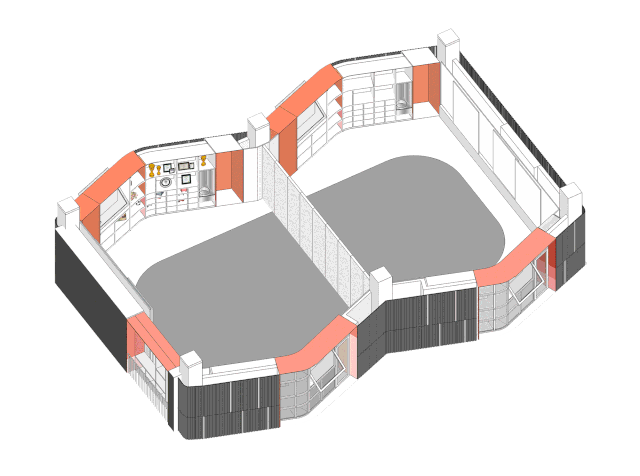
据了解,红岭实验小学的建设用地约100米见方,原规划24班小学,后因学位缺口巨大而增容至36班,现建筑面积约为原规划的两倍,建筑容积率超过3.0。“福田新校园行动计划”策划和发起人周红玫女士称,“这是传统校园规模的三到四倍,是规范的两倍”,在激增的教育需求与稀缺的土地资源之间矛盾明显的今天,“红岭实验小学的挑战显得意义非凡”。

策划和发起人 周红玫
在随后的主题论坛上,何健翔、蒋滢两位主持建筑师以“织造校园”为题,分享了源计划在深圳明德学院、红岭实验小学的设计构思。以及在城市剧变的背景下,源计划的设计理念——在项目里面首要的是“建筑师对自我、对城市的认知。所有源计划设计都在尝试回答这个问题”。

在问答环节中,张健、周红玫、何健翔、蒋滢分别代表使用方、策划方、设计方共同回应了在设计和实施中面对的重重困难。深圳市福田区红岭中学(集团)书记、校长张健先生也在现场代表老师、家长和孩子们,对校园环境做出了评价——“非常欣喜,这种(教室)设计因为中间的隔断可大可小,是可变化的空间”,这种设计带来的好处是“上课形式变化无穷,孩子觉得好玩”。同时,他认为学校的设计回应了红岭集团办一所看得见“童年和未来”的学校定位。


正如活动主持人,《住区》杂志副主编李文海先生所言,“‘福田新校园行动计划’改变了僵化的校园建筑模式和教育理念”。“设计与生活”系列活动将会持续关注在高密度条件下,融合现代教育理念及场地自然景观的新型校园空间,带领公众走进更多有品质的新校园。

精彩问答摘录
李文海(主持人,《住区》杂志副主编):大家可能都比较关心类似这么一个非常创新的项目,有很多人会有疑问说这项目会不会是通过非常规的方式甚至说突破了规范才实现的?
周红玫:我告诉大家的是源计划逼近了规范的底线, 但是完全没有突破,所有的东西都还在规范的框架内。红岭实验小学已经是一个“现象级”的学校,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已经有60批次的团队来参观,还有15批次的团队在轮候,大家都想知道对学校僵化形象的完全性、颠覆性的突破是怎么实现的?大家不要抱着希望说是我们突破了规范。
我先交代一下红岭实验小学作为高密度“的背景。以红岭实验小学为例,原本24个班的建设用地通过两次增容扩充至36个班的规模,而且随着教育设施标准的提高和教学需求的多样化,单个教室面积的扩大和各种功能教室的增加。其总建筑面积是传统学校的3-4倍,是设计规范的2倍。对于规划部门来说,这是一个全新的挑战,而接踵而至的批量改扩建乃至整个深圳未来校园设计都将陆续面临类似挑战,又使得这一探索意义非凡。
我们以此“个案创新”为抓手,适时优化我们的规划管理机制。对于快速成长的南方高密度城市的新校园设计,需要从现有僵化的管理和规范中开放出一个弹性的讨论机制,且对特殊建筑个案的范式探索给予坚定的支持。通过高水准的专家工作坊和优秀建筑师的最有创造性的优选方案论证和校核指标,并寻求具体项目的最优解。避免规划审批“一刀切”。密度新高带来类型突破,使校园空间模式有脱胎换骨之感。另一方面,新校园减少退距,实现与周围城市社区互动共享,从而使得这种具有现代意识的社区共享型校园模式得以在全社会倡导和推广。
这点我要特别感谢龚维敏教授,他第一次在工作坊说的那段话对我来说是振聋发聩的。就像一剂强心针,他说长期以来,中小学设计乃至整个投资建造体系,学校本来应该是最丰富的类型,但慢慢形成了一种单调无趣的模式化设计和最僵化、最呆板、最单调的类型,他说整个系统已经是反设计的。
回到规范的问题,现场的建筑师很多,我承认规范的问题太多,在我国建筑的众多规范中,诞生于低密度时代的全国性学校建筑规范恐怕是最僵化的一类——没有充分考虑不同地域间的气候和城市发展差异。而由于其背后的体制和逻辑过于强大,对社会以及国内大部分院校的课程设计最大的伤害莫过于,纯粹的功用和规范成了设计(课程)的中心,规范大于一切,不满足即危险,禁锢了设计思维,规范已经成了大家的托辞,以致大部分建筑师丧失提问和分析的能力,不能回到建筑学本体问题思考,因而产生了巨量套路化的“强排”方案。建筑的核心被抽空后便只剩僵硬的规范和图则叠加的学校楼房。
就像张之杨说的,这个学校最大的示范就是源计划没有为规范设计,而是为孩子们设计。他们用惊人的创造力以及非常坚强的毅力为我们带来了这样一个高密度的“创新样本”,向我们呈现了如此生动与丰富的校园空间和纯粹而又贴切的校园美学品质。所以我向源计划深深的敬意,也希望大家再接再励,能够回到建筑学的本体认真思考,在源计划这种高密度样本之上更进一步。

李文海:在这个项目过程中,你作为使用方跟设计方跟如何沟通,包括在什么阶段参与,以及参与的互动是怎么样的?
张健:红岭是一个非常大的教育集团,但是办小学是第一次,所以我们的定位很高。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遇见了周局,遇见了源计划蒋瀅和何健翔,是非常好的遇见。跟周局的沟通更是数不清,周局很有情怀,她不仅是一个官员,她非常有追求。建筑师也一样,他们不仅有设计的情怀,更有教育的情怀。
在整个建设过程中,前期花的时间比较长,我感觉有一年半的时间。后来项目确定下来以后,学校方跟规划部门和设计单位的接触非常紧密。很多地方政府包括在座的很多设计师所承接的工程都是叫“交钥匙工程”,政府立项、发改立项,立项以后找人招标设计,设计完以后招标施工,施工以后工务署介入拨款,拨款以后,校长你过来,这房子建好了,给你了,叫交钥匙工程,说起来似乎给我们减轻了很多负担或者这个学校建得很轻松。其实这样做一定做不成一个好学校,一定是千篇一律,非常的落后。
这次红岭实验小学的定位有几点,一是因为这个学校是公立的,但不是完全按旧的计划体制来管理的,是委托管理的。二是这个学校是完全的新课程,教室里所有场景可能会和其他的小学完全不一样,而是全课程项目制、包班制的,这是目前国际上非常先进的做法。我们是办一所看得见大家童年和未来的学校,这个学校的定位就是要建一所新学校,这个学校的课程就是要学校的每一个空间都是灵动的、都是能够体现课程的空间,这个设计和学校的体制、课程高度的融合,这些在我们不断沟通当中推向最大化。
李文海:龚维敏教授对过去一长一段时间内单调无趣的模式化的小学校园提出批评,指出整个中小学设计的背景在国内是反人类设计的,或者整个投资建造体系是反人类设计的。我们非常好奇,请龚老师给我们解密。
龚维敏(深圳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其实当时说那番话有它特定的背景。先说明一下,我本人并不是中小学方面做过有很多经验的,我很多经验来自于教学和参加评审工作,当然也有作为家长的身份。当时我说这样一番话,是有一种非常直接的感受,特别是在教学当中觉得很多非常严格的规定以及对使用的惯性,这是一种很强的限制性,我印象当中看到的东西的确是非常千篇一律。
刚才周局谈到了,其实像红岭实验小学这个案例,是我们是作为新校园计划评委时较早的案例,我的感觉是非常震撼。当然在这之后我也参加过几次这样的工作坊和评审,也看到过还有很多其他非常好的设计。但就像刚才周局所谈到的,这个方案本身并没有对规范做很明显的突破,所以我感觉这个设计实际上给了一个高密度校园设计非常好的样板——在现行的规范下能够兼容环境做到这件事,我觉得对我来说是非常有说服力的。
今天我来看这个校园,给我非常强烈的感受是这个校园的开放性。这种开放性是一层层的,不是把它当成一个建筑物,而是一个开放系统,这东西非常有意思,而且我觉得非常成功。尤其是这些下挖的,半室内的空间。我对小学校园设计的理解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刚才校长也提到了,叫看到童年,因为小学校园是小孩们成长时的重要场所,应该能够给他们留下记忆的一个场所。我们在这个建造中能看到非常丰富的能够留在记忆中的场所构思和考量。
另外,我觉得让我感到非常感动的是设计师刚才的发言充满了感情,何老师对校园思考的点并不仅限于抽象的概念,有很多很丰富的想象,包括建构的语言、丰富的材料、细节的变化处理。这个建筑听说好象不到一年的时间建成,这也是非常令人震惊的,这也说明了“新校园行动计划”是一个完整的系统性的成功,从周局的策划到设计师、到校方强有力的配合和支持,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案例。
回过头来再补充一句,尽管刚才周局谈到我们在现有规范和限制条件下仍然能做出非常好的设计,但是从我个人角度来说,我还是希望我们能在那方面有所突破和更加宽松。如果审视那些规范,其实有相当一些并不是那么的合理性或者已经过时,比方间距的要求,甚至有一些层数的要求,并不完全有理性支撑。从更多可能性角度来说,规范方面能够有更大的松动,可能有更丰富的校园样式出现。